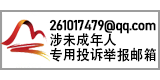巴州城东两公里处,塔子山如一轴青黛画卷舒展,山势蜿蜒,似长龙盘踞。山顶的凌云塔以直挺的身姿刺破云霭,砖石合砌的八角白色塔身,自百年前便俯视巴河,守望城郭。“登山则情满于山”,中国人最懂与山共情。塔子山是不少巴中人儿时的记忆,这里不仅有凌云塔、晏阳初博物馆,更有巴中人登山时于山水间情意的寄托。
登临山顶,巴城烟火尽收眼底。巴河如带,蜿蜒南去,山风掠过山顶,仿佛能看见百年前的古人登山遥相致意。
白塔与文脉

说起塔子山,自然离不开凌云塔。站在巴河边,看到一座白塔傲立峰顶,直插云霄,便知道这是塔子山了。这座山也因为这座塔而得名,如今已成为巴中的一处特殊记忆。
凌云塔始建于清道光十年(1830年),八边形塔身,砖石结构,十三层,阁式,八角攒尖顶,由地基、基座、塔身、塔刹四部分组成,通高43.33米,层层上收,塔内石梯为螺旋式。
进入塔内,沿着条石梯道缓缓而上,每一层有八个小窗,俯瞰巴城,各方位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塔内每两层便设有石造塔室一个,每一层塔室皆供奉有文昌星、仓颉、观音、关公等,雕龙藻井藏于其间,第六层的“二龙戏珠”铁铸八角藻井,铭刻着道光十年的匠心。
清朝文人白华封曾为此赋诗一首《凌云塔》:“客到凌霄气亦豪,诗题绝顶首频搔。清光倒泄山光活,碧汉横盘石气牢。妙在虚空能点缀,全无依傍见孤高。天留大笔图巴字,巨力凭谁一手操。”
围绕凌云两个字,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塔子山本身的雄伟,也表达了修建白塔主人的凌云之志。
中国多名山大川,礼敬山水是中华文化“天人合一”的重要体现。据记载,凌云塔的诞生,源于知州陆成本与乡绅的“振文风”之愿。凌云塔属文峰塔,意在培植地方人文地脉。塔身犹如一支巨笔直插蓝天,意在倡导巴中人的读书之风。该塔建成后,巴中近代史上出现了不少文韬武略的知名人士。
民间传说,凌云塔镇于“龙头”之上,以制水患,虽为戏言,却为山峦添了灵性。塔院碑板上的题刻——“共登青云梯”,是巴中人对文教兴盛的期许,亦是山与城的千年对话。
巴中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赵洪禄在《凌云塔赋》中赞道:塔名“凌云”,乃题名者志向之写真。吏辖一地,造福一方;功过是非,民心是秤。轻财方可聚众,律己足以服人。为官之道,深孚民心。云动宇宙弥宽,雨刷山川更净。
塔激发人的诗兴文兴,而人又赋予塔以灵性。
依托凌云塔,后来人们把辛亥革命先驱董修武烈士墓迁徙到这里,晏阳初博物馆也修建于此,张思训、严颜等巴中历史人物雕像矗立。
人说此塔,文脉传承更有承载。它就像一位白衣侠客,从容不迫地站在山巅,悠然俯瞰芸芸众生和沧海桑田。
晏园与传承

在塔子山上,与白塔一脉相承的,还有晏阳初博物馆。在山的一隅,博物馆静静伫立,宛如一颗被岁月珍藏的明珠。
登临山顶,俯瞰巴城,山风裹挟着历史的低语。晏阳初先生的汉白玉雕像矗立广场中央,他目视远方,仿佛仍在凝望那些亟待启蒙的乡村与人群。陵墓旁的石碑上镌刻的“除天下文盲,做世界新民”,既是他的誓言,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作为纪念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而投资修建的博物馆,晏阳初博物馆成立于1991年,总占地面积60余亩,建筑面积1200余平方米,目前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、馆藏最丰富的晏阳初思想研究基地。
步入晏阳初博物馆内的史迹展览馆,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,千余件文物与文献编织出一部平民教育的史诗,瞬间与历史相拥。
晏阳初的旧毛衣、手写笔记、泛黄的照片,以及张学良赠予法国小汽车(后被他变卖用于教育经费)的故事,诉说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朴素与坚守,印证了他的影响力。
最触动人心的是定县实验展区。1926年,晏阳初带领一群“博士下乡”,在河北定县提出“愚、贫、弱、私”四大顽疾,并以文艺、生计、卫生、公民“四大教育”对症下药。展柜中陈列的改良农具、乡村卫生手册,乃至一张张农民识字班的合影,皆是这场“泥土中长出的革命”的见证。
半个月前,清华大学“启梦川行”支教调研支队走进晏阳初博物馆,在这里了解晏阳初先生伟大的实践壮举,感受晏阳初先生对教育公平的执着追求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。这里是巴中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青少年们在“博士下乡”的故事中触摸历史的温度。
塔子山上四季更迭,展览馆内人来人往,而晏阳初先生的精神始终鲜活。正如美国女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其书中《告语人民》所述,晏阳初“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”。
塔子山与巴中

又是一年春意闹,正是踏青好时节。每年冬春交替之际,塔子山上的红梅都会竞相绽放,傲立枝头,弥漫着淡雅的清香,带来一片春意盎然。
踏上前往塔子山的路途,城市的轮廓在视线中逐渐模糊,而山的轮廓却愈发清晰起来。从远处眺望,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,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古代巴中人渴望文运昌盛、人才辈出,传说凌云塔能助学子开启智慧、学业有成,人们认为是塔子山的文气显灵,每年正月十六都会登山祈福,求文风更盛、子孙聪慧。今年,这里同样为市民游客们准备了一场精彩的登高祈福游园活动。在春日造访塔子山,不仅是怀古,更是文明进程的镜像。
从道光年间的砖石,到时至今日的红梅,塔子山承载的不仅是巴中的地理坐标,更是一部流动的史诗。登高望远,当万千足迹年复一年烙于山脊,在这座不显巍峨却深藏烟火的山峦中,编织出这片土地的文化经纬。
凌云塔下,历史的风华与当代的步履交织,山间每一片树叶的摇动,都是时光的注脚。晏阳初先生雕像静立山巅,目光所及之处,是文盲渐消的新民世界,是乡村重生的郁郁葱葱。这里不仅是历史的陈列,更是一盏不灭的灯,照亮来路与去程。
这或许就是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。几十年、几百年,铭刻一群人共享的记忆符号,勾连出一段关于“历史”的叙事。
不远处,巴河水依旧缓缓流淌,听风吹过塔刹的轻吟——那里藏着巴城的文脉与呼吸,与山河永恒。